品名篇佳作,观世间百态,享人文情怀
图文/赵正良 总编辑/方孔
【原创作品,未经允许,不得随意转载】
三十多年前的春城昆明,当云南师大校园的梧桐叶渐渐染上金黄,我第一次走进骆小所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课堂。彼时懵懂的我未曾预见,这场相遇将在岁月的长河中长成参天大树,其根系穿透时光的岩层,在我人生的每一处转角投下浓荫。先生立于讲台,身后黑板映着天光,温润的嗓音里蕴藏着力量:“修辞非文字游戏,乃心灵与世界对话的指纹。”这粒火种落入我混沌的学术视野,多年后方知,那正是先生对我“面授”与“神教”双重缘分的肇始。
面授时光:三尺讲台的精神雕刻
(一) 课堂上的思维锻造
早将王安石的《泊船瓜洲》背得烂熟,只觉其美,却难言其妙。先生于黑板写下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问道:“何以一个‘绿’字,令荆公涂改数十回?”当同学们纷言词性活用、色彩渲染时,先生却指向窗外玉兰:“看那花瓣边缘的光晕,‘绿’非静态之色,是春风拂过,整棵树自冬眠中苏醒的震颤。修辞之要,在于赋予文字体温。”这般将抽象理论具象化的点化,使我恍悟:语言学非冰冷符号,实为流动的生命体验。
先生的课堂从不堆砌概念,艺术语言在他口中如此鲜活!他常嘱我们留心观察:“看那爬山虎攀援的姿态,卷须如何与墙壁对话?此即自然界的修辞——生存智慧在形态上的具象。”云南山断水隔,民族众多,方言俚语如繁星。先生让我们在学好普通话之余,留心记录日常所闻的方言隐喻。我的笔记本上,至今存留先生朱笔批语:“‘日头辣得能煎鸡蛋’,触觉通感视觉,极富滇地语言的生命力!”
(二)师门夜话的思想启蒙
先生的家门向学子敞开。一个周末的夜晚,客厅里围坐着求知的青年。争论“艺术语言的审美特质”时,我固执于理论的严丝合缝。先生递来一杯普洱茶:“看这茶汤,清澈而有层次。追求逻辑闭环过甚,思想反失呼吸之隙。治学如沏茶,需沸水的激情,亦需陶壶的包容。”他曾展示早年研究手稿,泛黄纸页布满修改,红笔圈出段落,旁批:“此处过度解读,须回归文本肌理。”此等对学术严谨的躬身垂范,胜过万语千言。一次,我论文中夹带他人观点,先生未点破亦未斥责,只嘱我重读《文心雕龙》“修辞立其诚”,并言:“治学如做人,根须若歪,树干难直。”
(三)未竟的考研之约
大三时,我已沉醉于现代汉语修辞学,决意报考研究生。彼时先生尚不能带研,却倾力为我推荐川师教授,悉心开列书单,从陈望道《修辞学发凡》至西方隐喻经典,时时过问备考。然复习之路波折重重。身为寒门长子,就业与求学的天平在我心中反复倾轧。父母年迈,弟妹尚幼,家中虽未明言,那份期盼我尽早反哺的沉重不言自明。更添意外:暑期赴禄丰表哥处备考,水库游泳时突发腰部痉挛,身体直坠水底。昏沉之际,父母弟妹那期待而无助的眼神在脑中闪现——长子长兄的责任尚未完成!挣扎浮出呼救,复又沉没……醒来已卧岸边,幸得表哥相救。此劫后,虽复习未辍,心神已然不宁,效果大打折扣,终至落榜。先生知悉,未加责备,唯勉励勿馁,来年再战。
1992年南巡春风浩荡。毕业之际,我出人意料地放弃省城与故乡,选择奔赴边城河口。当向先生禀明此志,他眼中掠过深深的遗憾与责备:“此去,恐与学术绝缘矣!”沉默良久,他为我的杯中续上热水:“人生抉择无标准答案,恰如修辞中‘变体’与‘常规’之关系,重在抉择后的担当。”——后来方知,次年先生即可带研,我的选择却使师生之缘就此“绝缘”!先生终究未劝我回头,只于笔记本上赠言:“学术之门,永为向学赤子敞开。边陲沃土,亦能孕育独特的语言之花。”这句话,成为我日后在边疆熬过酷暑长夜时的精神图腾,每每抚之,如见先生期许的目光。
神教岁月:三十载的精神遥感
(一)边疆烛影下的文本对话
初至河口县农职业高级中学任教,学校深藏山沟七里之外。河口酷热,蚊虫肆虐,非亲历者难知其苦。风扇嗡鸣的夏夜,常赤膊备课。当教案写下“用比喻讲解语法”时,总忆起先生课堂妙喻:“语法是屋宇结构,修辞乃窗前插花。”讲解“借代”时,照搬教材例证收效甚微,忽记先生所言:“本土语言的修辞智慧最具感染力。”遂改用瑶族谚语:“吃土豆长膘,吃芋头长皮”,学生顿悟“土豆”借代“知识”之妙。那一刻,我方彻悟先生所谓“神教”——其学术思想早已化作种子,在我生活的异质土壤中悄然萌蘖。
(二) 公文堆里的修辞自觉
次年调入教育局,后辗转县委办、政府办、宣传部,终日与公文为伍。初以为公文只需规范准确,辅以官话套话即可。然先生教诲的真谛随文字实践深入骨髓:公文亦非文字木乃伊,当有现实的体温。我的文稿日渐熨帖,领导赞其“有温度,有泥土味”。至此方悟,先生当年强调的“修辞扎根生活”,岂止适用于文学?实乃一切语言实践的圭臬。十年机关生涯,养成收集方言词汇之癖,笔记满载百姓妙语:“政策落地要像春雨,不能像冰雹”——此等鲜活表达,成了撰写讲话稿时最珍贵的源头活水。
(三)书海深处的学术朝圣
2003年,通过公选进入红河州图书馆工作,终得系统研读先生著作之机。梳理先生学术年谱,渐次深入其艺术语言学理论体系。骆先生以其理论、方法、视角的多重创新,构建起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宏伟殿堂。其独特而丰赡的体系,为我们洞悉语言与艺术之奇妙关联开启新窗,为探究语言艺术功能提供系统指引,深化对语言本质的认知。它不仅丰富了语言学内涵,亦为文学、艺术诸领域注入新视角与新方法,其重要价值与深远影响,已超越学科界限,惠及海内外学林。
师恩如灯:穿越时空的精神光轨
如今,我的年岁已逾先生当年授业之时。以馆长身份立于图书馆阅览室,见年轻学子伏案苦读,心中暖意顿生。阳光穿过玻璃,在书页上筛下斑驳光影,恍惚间重回三十年前的课堂——先生立于讲台,话语清晰如昨:“语言是存在的家园,修辞是回家的路。”这条路,他以“面授”为我指明起点,又用三十载“神教”让我彻悟:真正的师恩,是点燃学子心灯,使其在漫漫长途中,既能照亮脚下崎岖,亦能仰望星空浩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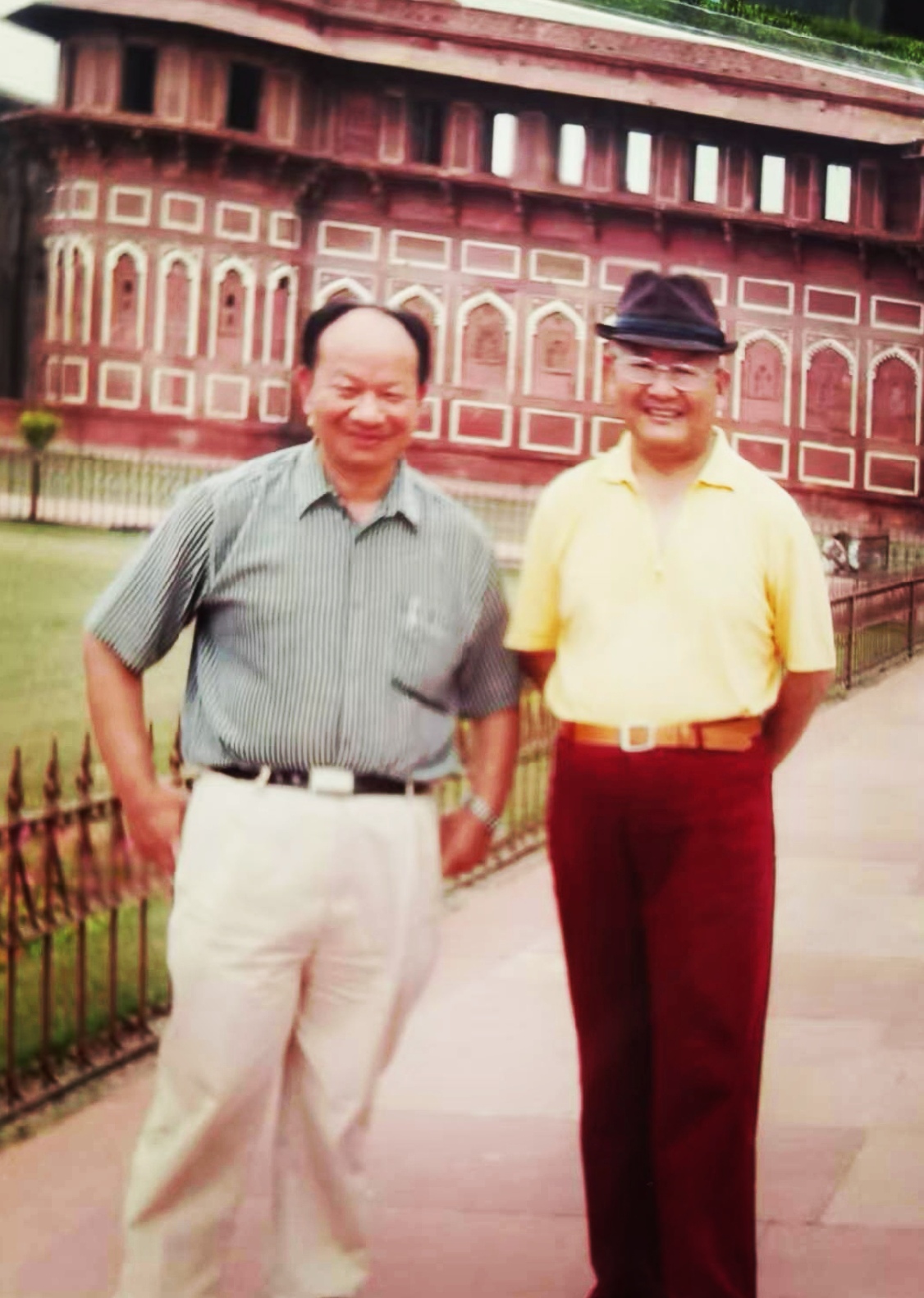
灯盏永续的精神长河
从师大的梧桐荫下到边陲的深山河谷,从公文的案牍劳形到典籍的书山册海,先生的教诲如一条隐秘的精神长河,在时光深处汩汩流淌,滋养心田。所谓“面授”,是知识的薪火相传;所谓“神教”,是思想的基因赓续。
先生曾言,研究者的境界,根植于其对国家、对时代的心灵境界。唯怀赤诚家国、拥抱时代之心,方能捕捉那无形之精神,领略人生别样的韵致与美丽风景。研究者当热爱事业,知足常乐,方能在清苦中活得舒展,在耕耘后收获喜悦。若福中不知足,则快乐与幸福终将遁形。于研究者而言,人生最美的风景不在终点,永远在路上。先生强调,学者当以创造精神为魂,将时间、精力、智慧倾注于社会事业。大学教授尤应以新知融入社会,从中获得精神回响。精神财富的利息非归己有,而永存于社会,推动其发展与进步。人人如此,社会方能累积丰厚的智慧资本。研究者对社会的理论贡献,便是其人生最美的风景。人生是一场修行,炼心方得无忧。

深夜捧读先生文集,窗外月色与案头灯光交融,仿佛看见先生当年伏案的背影。师恩如灯,照亮的何止学术的幽径?它更拓展了生命的维度。它教我懂得:语言是意愿与思想的桥梁,是灵魂的诠释者;语言学研究非书斋里的智力游戏,是对生活质感的深情触摸;教育的真谛,不在于知识的灌输,而在于灵魂火种的点燃。
如今,我常对年轻学子说:“治学当如先生——将根深扎于生活的沃土,让思想生出翱翔的翅膀。”这或许是对先生最好的感恩,亦是对“面授”与“神教”最真的传承。在这由智慧与精神铺就的漫漫长路上,先生的灯盏恒久明亮,指引着后来者,在语言的璀璨星空下,走出各自光芒夺目的轨迹。
作者简介
赵正良,1969年4月生。199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,师从骆小所教授修习现代汉语修辞学。毕业后志愿赴边疆,分配至河口瑶族自治县农职业高级中学任教。翌年调入河口县教育局,后相继在县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、县委宣传部、县文联工作。2003年11月起任红河州图书馆馆长至今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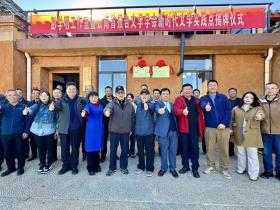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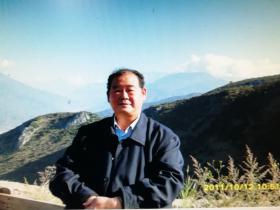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