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中国头条通讯社广东讯(记者 张兆伟 陆丽萍 通讯员 鹿禾)近日,《小小说选刊》《百花园》编辑部与华夏小小说研究院联合评选发布"2025年度小小说十大重要事件","鹿禾评刊"位列其中。评委会指出,2025年微信公众号"鹿禾评刊"构建"创作者-编辑者-评论者"协同生态,全年发布评论126篇,累计点评小小说作品1300篇次,以网络短评扩大小小说文体影响。
据了解,2026年,《鹿禾评刊》迎来全新升级,全新开设报刊拾微专栏,创新推出"作品+评论"双轨并行模式,为近三个月内发表的小小说搭建"二次曝光"平台,同时面向全国各大报刊征集2025年度优秀小小说并撰写深度评论助力传播,携手全国各大文学社团与小小说学会,通过解读、评论、传播共建文学品牌。
在此平台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投稿,关注《鹿禾评刊》!作品可直接发至编委会邮箱: luhepingkan@163.com。其平台长期招募执行主编、首席编辑、特约评论员。欢迎热爱小小说创作与评论、认同团队理念的师友加入。期待与业界同仁继续同行,为小小说事业的繁荣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!
据平台负责人鹿禾先生介绍,小小说的生命力在于被看见、被讨论。今年《小说选刊》第一期选取《年夜》《湖杀》《土》《懂你》《逃逸的苍耳子》《良缘》等小小说,题材开阔,涉及亲情、权力、怀旧、伦理、成长。作品手法纯熟,在叙述深处折射生活光影,细节不乏动人心弦的地方。读罢,我竟感到了一种倦怠。不是故事不好。故事很好,它们太工整了。结构周全感情圆满,转承起合都十分讲究。但正是这周全,使我嗅到某种文学天性在缺失。
小小说本是文学的刺客,要精准要致命一击即中。而这些作品像是彬彬有礼的文员按时到岗程序周全,少了冒险气。篇幅短字字不能随意。评价小小说不能说“这是一个好故事”,而要问它在狭窄的空间里,打开了新天地没有?“小”不单纯指体量的微缩,是精神的极度凝缩。作者要像雕塑家,一凿下去只留最迸发火花的那个截面。而不是用委蛇的情节填充所有的缝隙。
这或许是种受限的微观制约。一旦突破,小小说就破茧成蝶,获得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。方寸地,自有大道义。它必须承载观察与洞察在短促中营造可信心理空间。靠细节呼吸,靠留白生长,而不是靠情节的堆砌硬写。说白了,小小说若不敢冒险,再精致也只是安全装饰。

一、《年夜》双线叙事的亲情深描与意象反思
《年夜》是一篇用心的家庭叙事作品,处处可见作者对情感的珍视。作品运用时空对照手法,描绘出除夕夜父子间的思念之情。采用双线结构,一线位于新疆沙漠的钻井队父亲工作之处,另一线在沿海城市儿子与母亲包饺子之地,讲述了父子在不同空间共度除夕的故事。
作品对情感张力的构建是敏锐的。可惜,它被过于工整的对称结构所困。时间标记太精确,十点一刻、十一点半、十二点到了、十二点来临的时候,生活的粗糙颗粒感消失了。叙事成了两条独白端坐陈列。同步,成了它最大的问题。若真彼此思念怎会如此严丝合缝?父亲举杯时,儿子或许正与母亲争执;儿子回忆童年,父亲或许在咒骂着沙尘暴。错位失衡这恰恰是生活真实肌理,也是小小说最该闪光的地方。这里平行线叙事消解了情感应有的冲击。
个别细节是可贵的。儿子回忆父亲教骑车时悄悄放手、身影缩为黑点,以及视角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微妙转换,值得赞许,作者抓住了瞬间洞察力。笔记本原可以成为叙事的转折点,如通过电话提起笔误,儿子在电话这头先是一愣,随后两人都笑了。或者父亲在翻看稚拙笔迹,发现在折痕深处,还有一句更小更歪的“早点回来”,而后彻夜难眠。既避开直白的情感,让读者在化解误解中体会父子间的羁绊。让笔误成为父子情感沟通的障碍或桥梁,可它被谨慎对待简化为记忆的证物。像标本静躺盒中,没有成为推动情节的戏剧性转折,实在有点浪费了。
小小说要求把细节转化为生动的叙事,承载住生活温度才有分量。饺子是团圆的象征,可以融入叙事中。如儿子把饺子包成怪状遭到母亲的调侃,继而想起父亲离家时微驼的背影;或父亲在荒漠中庆节,嚼着羊肉默默念叨“还是家里包的饺子有嚼头”。更遗憾的是烟花,本可以藏着巧思。城市禁令取消了烟火,远方的父亲却想象荒漠上空熊熊烈焰。即可展开为现代性对传统情感的规训或抵抗。无声的除夕,如何成为父子的共处体验,儿子可以在电话里说今年真安静,父亲却答道我这儿倒是听得见鞭炮声,虚实交织的思念或许会更刺痛人心。但作者只是轻轻带过。
语言也过于满了。父亲回家的日子就像节日一般、沉甸甸的思绪等句子有点直白冗余。小小说需要的是精确、隐喻饱满,关键在于克制。沙漠中的父亲似乎看见了儿子模糊的脸,此句可在此收住,不用再补白“老齐也想他的儿子了”。这样反而削弱了若即若离的怅惘。小小说怕的是情感满溢,有节制的留白才可以让读者在沉默中感知和联想。刻意执着于温暖场景的话,容易把话说透,就偏离了趋近艺术而不求完美的手工艺守则。
二、《湖杀》反腐小说的批判深度与叙事界限
《湖杀》是一则讽刺批判之作,剖析了官场腐败与权力博弈。小说把背景设在古代,由湖泊建设切入,讲述了奎县王县令为了政治目的,迫害廉吏终遭报应的故事。作品戏仿官僚话术,写得很有意思。如王县令建湖四大理由、赵师爷的应景诗作等,都生动揭示了某些地方虚荣政绩工程背后的荒诞滑稽。
小说的前半部分批判是锐利的。王县令以工程为名杀害正直官员,强拆、谋杀、腐败等剧情撕开了权力的暴力本质。三个被杀的官员死的理由从惹恼了县令到“实在没理由了”,绝妙的递进,权力耍起横来连借口都懒得编。可作者并没有顺着这根线往下挖,结局三个被杀的官员化成鬼魂,削弱了整体批判力度,暴露出面对现实矛盾的无力感。化为轻飘飘的民间寓言、聊斋故事,可惜了。
还有视角的选取。小说始终跟着县令、师爷、知府打转。老百姓呢?死伤民工只用“几十人”带过,被毁的良田也就只是个数字。老百姓成了沉默的背景,连一声疼都听不见。站在高处批判容易,难的是俯下身听听那些被碾碎的声音。如果换个角度,比如从一个被强征去挖湖的农夫写起,或从一个守着被淹田地痛哭的老妇人眼里看去,或一个被强拆村民在瓦砾中翻找亲人的微小物件……那这场造湖大业的残酷,会不会更具视觉冲击?微观视角才能赋予批判以血肉气息与温度,内在挣扎远比外部批判更有张力。
细节方面有亮点。对官僚修辞的讽刺犀利,“生命之源”“皇恩浩荡”“不可估量”“县令挥汗筑堤坝,万民感颂逢清官”,既雅又俗,虚伪尽显。可惜笔锋一转,这些细节沦为了背景或闲笔。文中轻描淡写提了句,“奎县总是阴天、刮风、下大雨,但造湖一天也没有停止。你看,连天公都作难,人却拦不住,这种蛮劲里头有多少荒唐?”本来是小说最亮眼的刀子,但只把它当背景写了。若深入描绘农民在强制劳役与淤积怨愤中的具体境遇,叙事的深度将截然不同。细节的真实性,本就是批判力量的根基。
语言上也有遗憾。“唤湖”这个名字本来可以多做点文章。唤是唤水,是唤魂,也未尝不是一种呐喊。用湖暗含对清廉的反讽记忆,若让王县令醉后对着湖水喃喃自语“唤者何也?”但作者没从这份精神分裂般的恍惚展开,而是赶紧用一场热闹的显灵把场面撑满了,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现代性。热闹是热闹,味道却淡了。
回过头看,《湖杀》的尴尬或许也是很多同类写作的困局。想写权力之恶又不敢或不愿撕开最真实的肌理,走到半路脚下就虚了,转身逃进因果报应的安全区。真正的批判,需要有扎进混沌现实的勇气,也要求叙事本身能承受住那份沉重与复杂。鬼魂可以吓死一个县令,却吓不垮造就县令的土壤。这篇小说差的那口气,大概就在这里吧。
三、《土》乡愁意象的叙事张力与语言探索
《土》是一部以城乡迁移为主题的乡村叙事作品。这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对一袋乡土的情感变化历程。开头挺有味道的,儿子要进城,父亲偷偷往帆布包里塞满故乡的土,说是能治水土不服。这篇小小说具备探索精神,根系与离乡主题潜力,在意象营造、时间处理以及语言风格上有不俗展现。
这袋土,是赋予厚望的二十年乡愁。这包土从山脚菜园灶坑各处收集,带着老家烟火气,像个沉默的护身符。选土作核心意象,眼光够准的。故事往下走,这包土却越来越像一件道具。呈现方式太静态了,时间线也扁平,这个沉重的象征没有真正深入人物内心。
核心问题在于土地始终是被动的。种花、枯萎、丢弃。一套流程像预设的怀旧仪式,但沉甸甸的乡愁怎么就被处理得这么顺手呢?我心里那点期待跟着土一起丢空了。我总想着,那土种出的不是悄然生长的普通花草,而是老家院墙外那种没有名字的野花草,来到城里阳台开得怯生生。甚至它出现在最不经意时,某天孩子玩泥巴,妻子顺手掺了点土,孩子突然说“这泥巴怎么有奶奶家的味道”。不经意的瞬间思想闪回才扎心,更能扣人心弦。
要是作者敢让这土失灵一次,哪怕儿子某次生病时喝了土熬煮的水却吐得更厉害,或妻子无意中用它补墙却发现根本糊不上。偏方与现代生活的错位,可能比现在悬着的象征更有力。这袋土成了多余摆设,像个尴尬礼物。静态处理应为主动塑造人物命运服务,一旦变做被动客体,便无力在读者心中构建动态心理图像。
时间过得像翻日历。两年过去、又几年后、一晃二十年,父亲老了、村子拆了、成了家买了房……时间线拉得直,缠绕的情感却消散了。小小说的魅力恰恰在于要定格某一刻并深入挖掘。试想父亲去世那天,主人公失神盯着花盆中龟裂的泥土发呆;或是某个加班的深夜,他擦手时指缝间若有若无的土腥味忽然触发回忆,离家二十年的痛楚瞬间坍缩成一个尖锐的痛点。平铺直叙像在听会计报账,数据清晰却失滋味。可运用时序折叠跳跃,或将一个关键瞬间压缩出来,叙事张力会全然不同。提升节奏掌控,这才是小小说的创作艺术。
语言也有些温吞。“一串银铃般的笑声”“飘飘洒洒的柳絮”,这些表达如旧课本的灰尘模糊而失焦。怀旧叙事最怕的就是笼统的抒情。父亲从灶坑取土,那土是不是还带着余温?院子里挖的土是不是混着鸡粪和草根的气味?这些具体到刺鼻的细节,才是对故乡的真实记忆。那袋土本该带着汗味、粗麻布袋的触感,陪主人公从宿舍到出租屋再到新家阳台,每次搬迁都像不肯褪色的那场旧梦。可惜土始终是被处理的,没有主动塑造命运力,违背了细节驱动真实的创作原则。
于是,主人公面对空花盆突然哭泣的场面便显得突兀。结尾“突然之间”这个词,也暴露了前头的铺垫不够。情感需要铺垫,如果反复提及“爸的院子还潮吗”,对建筑工人的具体吩咐,在阳台刻意留位……层层递进,主人公的崩溃才有感染力。否则,就如演员被推上舞台按照指令潸然落泪,而台下的观众却嗑着瓜子,一脸茫然不知是否该随之一同悲伤。
真正乡愁,不是那袋被取走又丢弃的土,而是长期混入血管的沙粒,总爱在人生最顺当的时刻突然磨疼你,是一种延宕的缓慢的苏醒。小小说光芒或许应绽放在这样的心理根基上。
四、《懂你》家庭伦理的温情叙事与情感深度
《懂你》是探讨家庭伦理与生死的叙事主题。老王得了癌症,先是硬扛着不住院怕拖累子女。后来主动住进医院,理由竟是要给孩子们一个尽孝的机会。前提很感人,是不是?可描写稍简单直白,未能营造出令人信服的心理情境。最后他在病床上一脸安详地走了,留下老友老胡向儿子解释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心里总硌着点什么。
细节的处理可以更锋利。老胡看报告时叹气,摇头,轻蹙眉头,很好的切口足以剖开职业责任与个人情感的挣扎。那一下蹙眉里包含多少层意思?医生听到绝症患者谈钱的职业敏感,朋友间的欲言又止,或者被这句玩笑话刺到的瞬间无措?但作者一笔带过了。潜在涌动的远比直白的说教更有力量。
生活的真实纹理往往藏在欲言又止的细微处。这个家里怎么总在反复“开玩笑”,原来可以深挖成破碎式沟通的尖锐呈现。不过这还挺写实的。老王儿子在电话里反复开玩笑来化解话题,很多中国家庭沟通就是如此。但作品没有打破那层玩笑壳。试想下,儿子整理遗物时,突然发现了父亲笔记本上有那么潦草一行,你会怪我吗?这未说出口的回响,比任何解释都更沉重和有分量;或者想起老王曾经一句“我开玩笑的”,以致儿子在葬礼上莫名发笑却拼命压抑,可能更刺得人坐立不安。这类粗糙的真实,可以直击人心。
情节设计略显工具化了。给子女尽孝机会,这前提看似高尚,细想却令人不安。它把个人临终,变成了一场家庭关系的表演。父亲临终前还要操办子女完成伦理任务,子女的孝又需要特定场景来证明。这真的太累了。真实人性远比这复杂。老王可能因剧痛而突然向儿子发火,儿子或者在数夜无眠后与护士爆发争吵冲突。不完美瞬间比平静对话更贴近生命真相。这比一脸安详更接近真实。
再者铺陈太多,好多句子都在试图说明,失去了含蓄与余韵。小小说对白应如冰山的藏和露,成了直白信息输送。老胡最后指示像念手册,良苦用心会让人物扁平,损害了生活质感。潜文本浪费令人遗憾,“你爸当初不住院是怕连累你们,后来住院是给你们尽孝的机会”。要知道,家庭中动人时刻往往存在于理解缝隙里,而非理解本身。
说到底,《懂你》太想“懂”了。要把亲情说清楚,想把伦理摆端正,又把死亡处理得体体面面。但生活哪有条理分明呢?那些最深的感情,往往藏在“不懂”里。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父母为什么那样固执,子女之间为什么那样疏离,亲人临终子女各种愤怒、愧疚、解脱、麻木的所有复杂情绪都交杂着。好的家庭故事,不是给我们如何正确相爱的说明书,而是带我们走进那些昏暗的、说不清、有点难堪的角落,然后告诉我们:看,我们就是在这里。我们笨拙地靠近彼此。
不完美伦理的呈现,正是小小说的焦点,也是构筑真实心理景观的根基。作品如同熨烫过的衬衫,每个扣子都工整扣合。但真实的亲情,可能更像是那件洗得发软、扣子掉了两颗,即便失去光泽破旧,却怎么也舍不得扔的睡衣。它不够体面,但贴着皮肤的那面,全是生命和生活的温度。
五、《逃逸的苍耳子》以童年滤镜为视角的实验性叙事
这是一则以第二人称,展开混乱童年记忆的实验叙事。以缠绕的意识流语言,深入女孩童年时代的心理褶皱,勾勒出她被同伴蛊惑与抛弃的复杂记忆,以及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我感知力。
这篇小说是本期中敢于在形式上做明显突破的作品,其语言实验的意图清晰可见。这种形式的探索,在试图贴近童年混沌经验同时,不自觉地叠加了一层过于清醒的成人滤镜,未能捕捉到童年经验的真实性,使得叙事的实验性产生了一道微妙的隔膜。视角错位与漂移,阻碍了为读者营造沉浸式心理空间的目的。
第二人称的叙事,本是为了拉近读写的距离,却常常在不自觉推远。以成人的认知覆盖了童年的视角,反复使用坚信、想象、觉得、清楚、猜测、伤感等词汇。一个孩子只会体验到被窒息之感紧紧攫住,因为玩伴突然散去而愣在原地,而不会使用感到被抛弃或经历背叛这类精确概念。这种用词的精确,恰恰暴露了距离。看似邀读者代入,却变成内在的自我剖析,无意中制造了距离。那种属于童年的、毛茸茸的生动感反而被削弱了。
意识流技巧解放了语言,要求连贯与深化,否则叙事容易碎片化情感漂移。小说开篇便以独特的语感将读者带入一种潮湿、黏腻的童年氛围:“刚下过雨,泥和草的腥臭味膨胀,你的鞋底变得沉重”。确实捕捉到了童年记忆那种非理性、弥漫性的特质。童年叙事的最大挑战是重新沉浸其中,而非单纯回忆。作者有此意图,后面却未能彻底摆脱成人的认知结构。
当然,作品不乏动人的细节。“红塑料袋卡在下水沟的一株杂草上,被风吹得哗哗响”。这个意象生动地捕捉了被困孩童的恐惧焦虑,既无法挣脱又无法安宁,只能发出空洞而无意义的声响。这些瞬间。可惜它们孤立存在,缺乏重复与变奏。未能形成统一的心理气场。值得玩味如,祖母将摔倒归咎于营养不良,母亲说是用眼不当,不同代际的解释为相异的生活哲学。若作者有意顺着这线索,将“摔倒”发展为反复出现,让外婆的药汤、母亲的呵斥与“我”的自我怀疑形成复调,历史纵深感将会显著增强和丰富。文本仅触及情感表层,未能把握童年经验的本质,也未能为读者构建可感知的心理图景。
语言也过于规整。迷蒙眼神、随意举动、柔焦滤镜的表达,磨平了童年的粗糙棱角。童年不是田园诗,它应当承载着祖母竹杖的刺痛、母亲责骂的声浪,以及玩闹时膝盖擦伤血痕。抹去这些,童年就成了被过度修剪的诗篇,失去了真实的欢笑与泪水。小小说所要求的语言精准,在这里被诗意的模糊取代。“软的、妥帖的”“施施然”“你是莽撞的、坚硬的苍耳子,沾人一裤脚,会被爆裂地甩掉”“你的黑眼仁捉着这个黑点”,这类句子比喻精巧。语言风格与童年经验之间的错位,让心理氛围显得做作,剥离了真实的质感。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,作品似乎试图以形式实验,掩盖内容的单薄。第二人称、意识流、碎片化叙事。这些技巧本身无过错,应服务于对童年经验的深度探索,而非仅仅成为装饰点缀。一个认知的过滤器隔在了形式与经验之间。读者能感觉到创作者在“表演”童年,而非真正回到童年。
《逃逸的苍耳子》的探索勇气值得肯定。它提醒我们,小小说在形式与语言上拥有广阔的实验空间。技巧可以精湛,但若缺乏真诚,便会损害作品的真实与可信。如果“苍耳子”能够作为一个反复出现的、侵扰的物质存在,嵌入叙事各个缝隙,比如粘在主人公的袜子上、头发里,被她愤怒地扯下又好奇地观察等等。形式优美,却脱离现实,阻碍了读者的沉浸。小小说的内核,应是真实可触、可感的心理世界。童年呈现与童年经验的错位,让整个叙事成了精心编排的独舞。当形式与童年经验水乳交融时,那个“逃逸的苍耳子”,或许才能真正击中我们心中那片从未完全驯服的荒野。
六、《良缘》青梅竹马婚恋故事的叙事视角与语言风格
《良缘》是一部从童年玩伴视角深入探索婚姻家庭的作品。讲述了林豆豆与罗大佐的故事,二人自幼便被邻居戏称为夫妻。玩笑开了半辈子,最后他们真结了婚,可等到婆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,却认不出眼前这个“儿媳妇”了。陷入了假真假的循环模式。“儿媳妇”这三个字,是贯穿整篇小说的轴。它让人想到,多少中国式婚姻,不就是被这样半真半假的玩笑、被周围人的目光、被一种“大家都觉得你们该在一起”的惯性,慢慢捏合成的吗?
语言上,这篇小说透着怀旧气。“屁颠屁颠”“嬉皮笑脸”“气鼓鼓”,这些词反复出现,不免单调。少年的愤怒、羞耻与抵抗,远非这些词汇所能涵盖。看这段,林豆豆冲进教室喊“罗大佐,你给我出来”那一刻,声音是不是劈了?同学们瞬间安静下来,那种寂静是不是比笑声更刺人?这里作者有意磨去了文字的锋芒。而作为发生地的公共空间,带着计划经济的工厂食堂,本身是极具历史厚度、私事会被集体目光议论的场所,未被充分挖掘,如今错失了。
让我觉得可惜的,是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处理。婆婆把儿媳关在门外,认不出她了,这是多残酷的瞬间。可以引发对婚姻本质的锋利追问,如果最该记得你的人,忘了你,另一方该如何确认自己的身份?但这里,疾病仅用来构建最终的情感消解。罗大佐跑回来,没心没肺地问“媳妇,咱妈又犯糊涂不认你了?”最后以林豆豆那句带着哭腔的“你还管不管你妈”收尾。一切又回到了打打闹闹的温情频道,轻轻掩埋了如深渊般的问题。结局如停在婆婆反复问林豆豆是谁?然后沉默不语,记忆被放逐的荒诞感,会更令人刺痛。但艺术的创新不足,这就像眼看要揭开生活的硬壳,手却缩了回去。
全知视角方便时间跳跃,损失了有限视角的紧张感,故事其实可从林豆豆的固定视角带进,童年时候的误读,成年以后对罗大佐善意的迷惑,对婆婆病情的错误理解,一直到最终明白良缘真正含义的醒悟。那种被命运操控的无力感,真相大白时放下,可以焕发出实在的力量。可惜作者对象征性暴力刻画只是蜻蜓点水。它如何塑造人物命运?又如何营造出能攫住读者呼吸心理氛围?缺少了这些更深的挖掘。限制视角带来的那种笨拙和顿悟,有时候比全知全能更真实。
罗大佐后来成了社区警察,在社会角色里找到了权威。但在林豆豆跟前,他似乎还是那个“匆匆忙忙”的少年。这种外在权力跟内在自我的不协调,本来是十分引人思考的路径,故事却没有深入。当“天作之合”的剧本被记忆的橡皮擦抹掉,两个人最终有没有机会加以审视互相的真实自我?还是仅仅继续扮演命运分配的角色?这个问题,本来可以更强烈地提出来。
叙事视角的选择,使心理景观平淡了,缺少了咀嚼味道。
结语
阅读这六篇小小说,像一次温和的文学散步,沿途景色熟悉,偶尔有惊喜,却终究没有让人停步屏息的意外时刻。它们或许反映出当代小说创作的某种侧面,对“完整”故事的过度着迷,从《年夜》的对称时间到《湖杀》的因果报应,再到《土》的线性回忆,作者们好像遵循一份清单,小心谨慎地把每个情节点放进传统的叙事模板。
这种对“完美”的刻意追逐,反而限制了创作的自由,小小说的本质,本来不在于详细讲述整个故事,而在于在合适的时刻停步,留下一道缝隙,让读者侧身进入,当一切被解释得太过清楚,想象的空间就被完全占据。
形式上也显得小心,《逃逸的苍耳子》虽然尝试了语言实验,但多数作品仍然安于全知视角跟线性叙事的安全地带。意象变成简单标识,《年夜》里的饺子,《土》里的画布包,这些叙事静止,没能跟人物命运交融衍生出更深的意义。批判的锋芒被温情或幽默软化,《懂你》将生死简化为道德表演,《湖杀》借助鬼魂解决现实困境,都回避了对人性复杂的探讨。
然而,我仍更珍惜这些文字,它们对普通人悲欢离合真诚描绘,自有其内在力量,所揭示创作困境或许比其成就更有启发性。在一个推崇完整跟安全的文学格局里,小小说这一体裁是不是应当更大胆地拥抱其固有的“不完整性”。
这六部作品,标记着我们此刻所在的位置。犹如途中的界碑,更丰饶的创作图景或许就在下一个岔路口之外。那里属于敢于偏离主道的人。小小说的真正魅力在于化简约为力量,以小见大,在有限空间内引发有意义的震颤,凭借真实可感的细节营造独特心理氛围,并在批判与构建间保持温暖而锐利的锋芒。
这或许便是“技进乎道”所在。希望下一期,可以读到更勇敢一些的作品。
编审:观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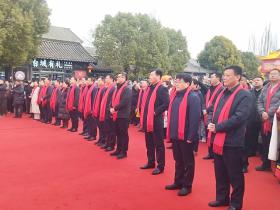







评论